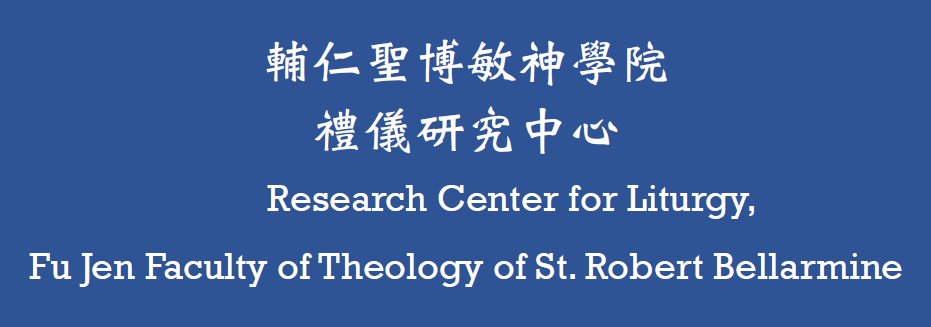聖樂之父Palestrina創作曲風
為今日華語教會的省思
在今年2025年,古典音樂乃至於聖樂界不能不提起一位偉人——號稱音樂之父及教會音樂救星的Giovanni Pierluigi da Palestrina。
如果相傳的出生年代正確的話,今年便是Giovanni Pierluigi da Palestrina冥誕五百週年。著名的古風合唱團(Stile Antico)為此特別推出了三張專輯,而劍橋大學克萊爾學院合唱團(Choir of Clare College Cambridge)同樣也為記念這五百週年冥誕,在近期發行的一張專輯中收錄了五首世界首錄。無論在古典音樂界或是在教會內,記念這五百週年冥誕的演出並不少見。在歐美,來自梵蒂岡,隸屬於The Cardinal Domenico Bartolucci Foundation的Sacred Voices合唱團巡演美國紐約;在東亞,Vox Antiqua於澳門聖老楞佐堂獻唱了這位教會音樂之父的名作Sicut cervus。而在今年6月18日的一場由前述同一個基金會發起的Palestrina郵票發行的紀念活動上,教宗良十四世高度讚揚了這位教會音樂之父的貢獻。
Giovanni Pierluigi da Palestrina出生的那個年代,人們時以出生地來稱呼一位傑出人士,而他本人也曾有過一次以Palestrina來自稱自己;Palestrina座落在羅馬東方40公里內,舊稱為Praeneste,屬於教宗國。聖樂之父Palestrina的年代,正是宗教改革(始於1517)及特利騰大公會議(1545~1563)時期;在那羅馬風雨飄搖的年代,他的聖樂在人們心中注入了神聖和安定的力量,真是一條不折不扣、實實在在的通往上主之路。
在十六世紀的歐洲,伴隨著宗教改革而來的,在教會音樂的爭論上相當程度乃聚焦於複音音樂(Polyphony,簡言之即多聲部音樂)。複音音樂並非十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首創,早在中世紀歐洲修院中已經出現,及至中世紀末期的尼德蘭(荷蘭)樂派更是深化了其理論及創作技巧。當馬丁路德推動宗教改革時,將多聲部的讚美詩納進教會禮拜,且是採用地方語言德語詠唱,為能激起信眾的主動參與。相較於路德教派對於禮拜音樂的革新,當時歐洲天主教會在教會音樂上面臨的挑戰是:一方面是音樂家的創作水準需要進一步提升,一方面是必須審慎評估複音音樂是否適合在禮儀中使用。
宗教改革時期的教廷對於複音音樂的戒心其來有自。十四世紀初,教廷曾經移居法國東南部的亞維農(Avignon),當時屬於西西里王的冊封地。亞維農當地的發展中的複音音樂,可說是與音樂俗化劃上等號,以致於教宗若望廿二世於1324年發佈《教父們的訓誨》憲令(Docta Sanctorum Patrum),嚴加禁止並棄絕在禮儀中採用那一類音符猶如野馬狂奔、歌詞意義大受破壞,或加入戲劇化動作取代宗教敬虔表現的歌曲(註1)。然而,亞維農時期面臨的音樂俗化弊端,那音樂的表現形式並非複音音樂唯一的可能性。
天主教會在特利騰大公會議時期,在聖樂革新上,一方面是發佈法令,不可採用俗樂曲調作為彌撒曲的主題,此外,亦要求作曲家不可因裝飾對位或模倣對位,而致使人無法瞭解歌詞意義(註2)。二方面,委託作曲家按照大公會議對聖樂的要求創作禮儀音樂,以證明複音音樂不一定會破壞禮儀的寧靜。於是,作曲家Jacobus de Kerle受德國Augsburg主教Otto樞機請託,創作了Preces speciales pro salubri generalis Concilii succesu(《為大公會議成功特殊禱詞》);這首四聲部禮儀音樂,各聲部明朗,且因採用較多主調音樂式而讓歌詞能清晰為人瞭解,整體表現溫和虔誠,堪稱典範(註3)。此外,於1570年出版彌撒曲集Missae quatuor concinate ad riyum concilli Mediolani的作曲家Vincenzo Ruffo其本人便在序言中說明,這曲集毫無俗樂素材,是完全符合大公會議要求——為使會眾瞭解歌詞(註4)。
傳說中,Palestrina因著創作Missa Papae Marcelli而挽救複音音樂免於被取締而不能在禮儀中使用的這說法,在著名的學者Franz Xaver Haberl考證之下,發現可能並非史實;同一首彌撒曲遠在出版之前已在聖母大殿以及西斯汀歌詠團的檔案裡出現(註5)。再者,Haberl認為當時教會內聖樂的革新,重點應是在於歌詞的純清以及歌唱方法的改進,而非完全摒棄對位法(註6)。若說前述的Jacobus de Kerle以及Vincenzo Ruffo兩人的傑作解除了複音音樂採用於禮儀的顧慮,那麼Palestrina則是將複音音樂的藝術性推向顛峰。他將理論及形式實現在樂曲創作上,形成一個有系統、有邏輯的規範;他不止一個人獨自名留青史,更是影響、提攜了許多追隨者及後進晚輩,共同努力成為具有特色的「羅馬樂派」(註7)。Gregorio Allegri——譜曲那首莫札特十四歲時默寫的Miserere mei ——也屬於羅馬樂派(註8)。
整體來說,文藝復興時期的聖樂作曲家均能以成熟的對位技巧,將額我略聖歌曲調融入複音音樂體裁,而被教會接納為禮儀音樂(註9)。他們主要根據中世紀以來的八個主要教會調式;採用自然音階式的歌唱體系,且旋律進行由「級進式」主導;旋律節奏依照散文式拉丁文聲點;旋律外型一如說話的高低起伏;旋律句法依循文詞結構法則(註10)。Palestrina的特色就在於:無論聲部多寡,每一聲部表現往往呈現出拱形,且旋律均以級進式為主導,縱然有些跳動都不至於太大,且嚴守規範,因此歌曲一如傳統額我略一般沈穩,且如語言般易唱(註11)。論其多聲部,雖從單旋律來看算是繁複,但是將這些各自獨立的旋律結合在一起時卻變得相當整齊;這種內在結構就如同建築一般完美,其所表現的是更具客觀性及普遍性,且奇妙的是,縱然其音樂是以自然和邏輯為基礎,卻不失個人情感的表露(註12)。
如果我們認同聖樂乃是為聖言而服務,便要特別關注聖言的詞與音樂要素之間的關係。教宗良十四世在今年6月18日的那場紀念會上高度讚揚了Palestrina的複音音樂。教宗肯定Palestrina的複音音樂實在是受了聖言神聖文本的啟發,並重申聖教宗碧岳十世於Inter sollicitudines第1號當中說過的,「將聖言穿上合適的旋律」,以便更好地「觸及信友的智慧」。教宗又進一步說,複音音樂是將歌詞透過多聲部來實現前述目的;每個聲部各以獨特的方式,以多樣及互補的旋律以及和諧的動機來重複歌詞。作曲家巧妙運用對位法以使旋律互相呼應,即便有時採不和諧音,最終也會以新的和弦化解。教宗也指出靈性上的意義,他表示,複音音樂這種多元中動態的統一性,正象徵著我們眾人在聖神引領下共同的信仰之旅。複音音樂這種多元動態中的統一性,是為了幫助聽眾更深地領悟歌詞所傳達的奧秘,並在適當的情況下以應答或其他方式回應。(註13)
思量聖樂乃是為聖言服務,華人聖樂大師(Maestro)劉志明蒙席也指出,Palestrina的聖樂是在「語文節奏」的大原則下,將旋律線與文詞結合在一起,使它像語言的起伏一般;一方面,它不陷於機械式的呆板,也因著其拍子是內在的,是來自音樂與文詞結合的結構本體,故也不受現代譜節線劃分拍子的限制;二方面,即便在作曲上使用模倣對位技巧,亦能讓人清楚詠唱出來的歌詞的意義,這乃符合教會訓示中聖樂為祈禱而生的本意。(註14)進一步而論,聖樂透過詠唱而為聖言服務,故此,歌唱法這環節無疑是重要的;Palestrina本身對於歌唱法雖無明確指示,但按其精神,歌手不但要具備好的聲音,要能唱得準確,也要留意歌詞完美的表達,並能把持住歌曲中的情感表露以及強、弱表現,不可隨意加入自由發展的音符。(註15)
Palestrina逝世後,蒙教會安葬於聖伯多祿大殿內,墓碑上刻著”Joannes Petraloysius Praenestinus, Musicae Princeps”,被尊稱為「音樂之王」。(註 結語第四段)值得留意的是,這位音樂之王逝世時,床邊立著聖斐理伯內利(St. Philip Neri,司鐸祈禱會會祖,也是義大利神劇之父)的雕像(註16),這亦表彰著那個時代羅馬城公教世界共通的精神品味:認真舉行禮儀,重視音樂,研讀聖書並從事靈修談話。可Palestrina的影響並不侷限於羅馬城與公教世界,後世一流作曲家舉凡巴哈、貝多芬、華格納、布魯克納、威爾第、德布西等人,都鑽研過這位音樂之王的創作曲風;巴洛克時期奧地利音樂家Johann Joseph Fux還將這位音樂之王的作曲技巧編為教材用以指導學生作曲(註17)。
四、五百年過去了,十六世紀反宗教改革時期羅馬樂派的一代宗師Palestrina,其聖樂的曲風為今日的華語教會能帶來怎樣的啟發?首先,我們要先看一看所身處的實際情況。必要認清,我們所身處的是一個所謂「多元」的年代,而在實際的堂區牧民及禮儀生活實況中,一個相對應的現象就是大型堂口一個主日往往有好幾臺彌撒,而不同場彌撒的劃分有的是以會眾的屬性為考量。於是,我們就會看到,在同一個堂區裏頭,有古典派的,有新潮派的,有本土派或本位派的,有普羅大眾派的,此外還有青年及兒童主日學的。本文無意在此評估這現象究竟是好是壞,而是要指出,這種會眾區劃的現況,往往也反映在禮儀中音樂採用的選擇上。
先暫時撇開音樂類型的差異不論,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是:聖禮中採用的音樂,其評判的原則究竟為何。Palestrina的聖樂曲風一大特徵就是旋律與歌詞的美妙結合,而多聲部的作曲技巧又是為了幫助會眾更深地、更廣地體會歌詞中聖言的奧秘。就此而論,無論今日禮儀所採用的音樂是何種類型,在聖禮的機能上。其旋律都必須能夠清晰地傳達聖言,且聖詠員也必須具備足夠的本事,除了唱得準確,更要完美地表達聖言。走筆至此,我相信讀者都能夠判斷哪些歌曲達到要求,而哪些歌曲遠遠不及格。
為多數人來說,喜愛Palestrina曲風的人可能算是小眾。一個合乎理性的態度是,不要因為Palestrina及羅馬樂派是所謂西洋的,又是四、五百年前,就先入為主排斥它,而是要先放下成見,嘗試體會它究竟有什麼優點;這說成大白話就是:先暫時撇開音樂被貼上的標籤不論,而儘可能不存成見地去體驗音樂本身。
在今日這個嘈雜、焦慮、人心浮動的亂世,Palestrina及羅馬樂派的音樂可說是一帖福音良藥,因為那級進式的旋律進展與自然音偕體系,能助人體驗和諧,甚至增進身心健康;至於提升祈禱,那更是毋庸置疑。
我們不能強迫所有人都喜歡某種音樂,可是對於傳統中寶貴的精神資產,我們有其責任去延續,而Palestrina的聖樂便屬於這範疇。若您也喜愛,歡迎加入推廣的行列,這不但要讓人清楚認識到音樂之王聖樂的優點何在,更要引人體認,當年羅馬樂派的聖樂曲風,同羅馬禮的節制理性、適度有節,是不可分割的。
最後,我也要提出:當人們需要進入「非日常性」的朝聖狀態時,以Palestrina為首的聖樂寶藏無疑是重要的。
註
[1] 劉志明著,《帕勒斯替那與教會》(香港:公教真理學會,2009),11頁。
[2] 同前引書,26~27頁。
[3] 同前引書,27頁。
[4] 同前引書,27頁。
[5] 同前引書,29頁。
[6] 同前引書,29頁。
[7] 同前引書,45頁。
[8] 同前引書,84頁。
[9] 同前引書,99頁。
[10] 同前引書,100頁。
[11] 同前引書,90頁。
[12] 同前引書,90頁。
[13] https://www.vatican.va/content/leo-xiv/en/speeches/2025/june/documents/20250618-fondazione-bartolucci.html 以及https://adoremus.org/2025/06/pope-leo-xiv-praises-the-beauty-and-harmony-of-polyphony/
[14] 劉志明,《帕勒斯替那與教會》,結語第四段。
[15] 這是Emilio de’ Cavalieri於Rappresentazione di Anima et di Corpo序言中提及的。同前引書,結語最末段。
[16] https://jojoclassicalmusic.blogspot.com/2024/02/giovanni-pierluigi-da-palestrina.html?m=1
[17] 同上
敬祝 您們在聖禮的參與及服事中,走上成聖之路!
禮儀研究中心 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