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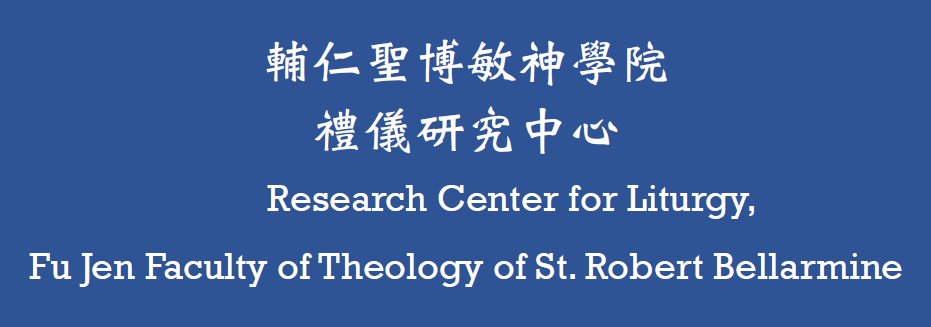 |
 |
|||||||
《禮儀人》電子報 |
|||||||||
以聖禮彰顯神聖是為一個召叫鄉愁 如果您熟悉十九世紀末至廿世紀前半的歐洲思想、文化,那可能對「鄉愁」這詞彙並不陌生。詮釋社會學大師馬斯‧韋伯(Max Weber)論及現代世界理性化的「祛魅」(entzauberung; disenchantment)時,感嘆終極價值的消逝,字裡行間總帶著鄉愁。哲學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無論在《存在與時間》中論本真時間意識,或是在〈詩人何為〉中論詩人賀德林筆下的諸神離去、世界基礎崩塌,字裡行間總帶著鄉愁。即便是法蘭克福學派的瓦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也在《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中評價大量複製技術使得靈光消逝,使藝術失去本真性(但透過攝影捕捉那乍現的靈光卻又是可能的),字裡行間總帶著鄉愁。總的來說,如此眾多的思想家「字裡行間總帶著鄉愁」,實則呼應著尼采所宣告的「上帝已死」;大致上來說,這是歐洲文明從啟蒙運動一路發展下來的趨勢,當上帝在多重領域被人類請出去之後,人似乎得到了想要的自由及自主,卻陷入了無家可歸的精神狀態之中。 對於華語世界中的我們來說,「鄉愁」一詞又帶著多義性。如果你的父母是1949年跟著國民政府逃難到臺灣的所謂外省人,當你在1990年代陪伴著滿懷鄉愁的爹娘重歸故里,在感嘆人事全非之餘,可能頓時發覺,那一個曾經的中國,如今是再也回不去了。如果你在1970年代爭取到獎學金留學美國,這鄉愁可能連在課業繁重的週末也不放過你,夜間你像個遊魂似的飄盪在又髒又舊的街道上,總覺得心裡頭空著一個洞,怎都填不滿;多年後當你讀到顧肇森所著小說《貓臉的歲月》,不禁老淚縱橫,你的兒子見狀,問說「爹地,你怎麼了?」說的已經不是中文,而是道地的美式英語。或許您都沒有這一類的切身經驗,但可能也經驗了其他類型的鄉愁。您兒時與鄰居小孩一同玩耍的小巷如今早已不復存在;您就讀的小學每逢盛夏總是一片黃沙滾滾,今日您雙腳踩著電梯大樓華廈的木質地板,回想起當年真是恍若隔世……而今,同一層樓的鄰居總是不打招呼,小時候鄰居即便是巷子對面卻也總是互通聲息。為您來說,鄉愁這氛圍,可能指向一個已然回不去的美好狀態,其中有著值得追憶的、具體的人、事、物,也有特定的場景供人憑弔;這鄉愁聯繫著您所珍視的重要事物,這一路推到最底,說穿了就是指向自身存在的根源。 在全球化的影響之下,我們華人在思想、閱讀、影音閱聽上或多或少也染上了近現代西方文化中感嘆精神上無家可歸的鄉愁;於此同時,我們也處理著自身的鄉愁,有的是國破山河在的鄉愁,有的是傳統價值崩解,或者是本位文化不敵全球化的鄉愁,有的是幼時熟悉的地景消失而致的鄉愁,有的是感嘆今日不如從前的鄉愁。如果梳理這些鄉愁,由外而內回到我們內在,或許能發覺一種擔憂自身又被歷史洪流支配的焦慮,那就是在生活世界的時間流裡,似乎有好幾股力量同時支配著吾人的生活方式,且還將我們拉離自身存在的根;於此同時,我們也感受到一種強烈的渴望,一種尋求歸宿,想要回到根源的、難以壓抑和熄滅的騷動,這若一路推到終極,那就將是渴慕神聖,追尋神聖。 進入神聖時間 與韋伯、海德格、本雅明一樣在字裡行間浮現著鄉愁,著名宗教學大師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則是在宗教現象學以及比較宗教的研究上,為二十世紀飽受戰禍之苦、反省自身存在意義的人類畫出了通往神聖之境的地圖;縱然其論述並非毫無缺點,其思想為二十一世紀的我們依然深具啟發性。 透過對於原始社會宗教現象的考察,伊利亞德指出,對於神聖的渴望,正可等同那對於存在根源的鄉愁;人類渴望回歸那起源的時間,也就是渴望回歸那諸神臨在,那恢復穩固、直接、純淨,和存在於彼時的世界(註1);這種對於起源的鄉愁,也等同於宗教的鄉愁(註2)。對照基督宗教,這鄉愁也可說是對伊甸樂園的鄉愁;自從人類被逐出樂園之後,再次回到樂園的渴望便未嘗停歇半晌。 時間向度是伊利亞德宗教研究的一條重要的內在軸線。按伊利亞德,時間可區分為凡俗時區與神聖時區。神聖時區即顯聖時間,承載著集體和個人的記憶,讓神話原型得以發生、重複,且讓人得以重返起源,回到原初——人性共通的普遍根源(註3)。某些儀式能夠打斷凡俗時區,而進入非歷史性的神聖時區;此正如教堂在都市的凡俗空間中構成一個突破點,儀式也在凡俗時區中構成一個突破點,使人能進入神聖時區。透過儀式的參與,任何人都能與起源的「那時刻」(illud tempus)成為同時刻的(註4);人在這其中,生命獲得重生與更新,不但保留了完整的生命力,更展開一段新生命,如同出生時刻一般。我們能就此引伸:當人類參與宗教儀式,進入神聖時區之時,不但生命獲得更新,原先困擾心靈的、屬於凡俗時區的歷史性的焦慮也要被解除。以宗教現象為例,玻里尼西亞人透過儀式性的誦讀宇宙創生的神話故事,使原初的宇宙創生事件再次臨現,時間便進入那世界的開端,而人便成為了與宇宙創生同時間的人;而生命因著回歸原初時間及象徵性的再生而獲得治療(註5)。 伊利亞德關於神聖時間的分析為基督宗教來說,儘管與原始社會宗教現象存在著差異,依然深具啟發性。教會禮儀日曆每年所重複的,主要乃聚焦於主耶穌基督的降生及逾越事件,而這既是歷史性的,又是奧秘的。曾活於歷史中的主耶穌透過完成救恩而更新了時間(註6),這救恩的奧蹟本身又是一個新創造。透過禮儀年度,我們連結主耶穌開創的救恩奧蹟,故舉行神聖禮儀就是不折不扣的神聖時間,舉行聖禮的聖堂就是空間上的突破點。在聖禮的神聖時間裡,因宣報救恩的大敘述(請回顧復活夜守夜禮隆重的聖道禮儀),以及舉行「你們要這樣做來記念我」的祭禮,我們進入了主耶穌救恩奧蹟的時區,與我們存在的根源發生連結,於是我們的生命再次獲得更新與再造,種種的生存焦慮也再一次被解除。 然而基督宗教因著上主的啟示,在本質上與原始社會的宗教現象是不同的。原始社會的宗教現象展現的是人性共通的、對於回返根源的渴望,而基督宗教所彰顯的是啟示者天主乃聖中之聖,是萬有真原,是今日依然向我們發言的上主。如果原始社會的質樸人們尚且那麼誠心追尋神聖,那麼蒙受救贖初果的基督徒又該以何等的熱忱追尋上主,重返神聖呢?! 以聖禮彰顯神聖在今日更是一個召喚 藉助伊利亞德宗教學研究的啟發,我們較容易擺脫既有盲點,以一種類似局外人的眼光來思索教會聖事禮儀所當何為;而透過比較宗教,我們也能明白基督宗教的獨到之處究竟何在。在那共通的人性深處,有著回歸存在根源、追尋神聖的強烈渴望,而教會聖事禮儀必須要能夠答覆這神聖的渴求,故此,聖事禮儀若要正中靶心,必須彰顯神聖。就此而論,教會聖禮的本質乃是關乎神聖,而這神聖並非那些出自臆想的供人膜拜的神祇,而是創造、救贖我們,愛我們愛到了底的天主,祂在聖禮的神聖時區內與我們親密往來,使我們的靈命因著與救恩奧蹟同時間而在祂內再度更新。總的來說,人因著宗教性的鄉愁,追尋神聖,故參與聖禮,而聖禮也因著上主的臨在,將人進一步教育成為具有深厚信仰的宗教人。 在這地景變動迅速,記憶儲存在於電腦而不是泛黃日記本,許多人將因著AI興起而失業的量子電腦時代,我們渴望回歸根源的欲求應是比一百年前的戰間期更加強烈。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是歐美國家的一些年輕人更偏愛羅馬禮特殊形式,此即傳統拉丁彌撒;或許這些年輕人在其中感受到自己像是回了家一樣,因他們的祖先參與的正是這禮式(這不也正是鄉愁麼)。不可諱言,傳統拉丁彌撒在一些人眼中可能是老古板,但其祭禮卻因著強烈的上下垂直幅度,以及嚴謹的規範性,而瀰漫著一股無法言說的神聖感;相形之下,新禮彌撒的服務團隊及會眾若經過相當程度的調教及操練,彰顯神聖感也是做得到的,而傳統拉丁彌撒仍能提供相當的養分以充實我們的底蘊。 在講論聖禮的神聖感時,我們也應當要避免陷入那過份看重個人主觀情緒及宗教經驗(甚至無視於道理正確與否)的陷阱,這在1947年教宗比約十二世《天人中保》中已經被糾正(註7);傳統神修也告訴我們,一昧地追求一些獨特的體驗,有時易於遭受仇敵的欺哄而不自知;個人主觀感覺感受良好與經驗神聖這兩者間有時並非同一,而我們所要追求的,是被神聖者天主轉化、更新、再造,而不是只聚焦在感覺感受層面。任何的學科都必須回到客觀來探究事理,而基督宗教聖禮神聖感的根源,推到最根本,必定是指向那藉著儀節的舉行而臨在我們當中的天主。在聖禮的場域,天主的救贖工程持續工作著,祂那轉化的恩寵隱身在可見可感的儀節之中。沒有人經驗到天主卻不被祂轉化的,反過來說,當我們經驗到天主的轉化恩寵時,這正是不折不扣的與天主相遇的神聖體驗;就此而論,聖禮中的神聖感正是天主轉化能力的外顯。為我們這些屬於啟示信仰的基督徒來說,必須明白,神聖不是來自人自身的創造,而是來自天主從上而下的啟示行動。正如《上主的話》宗座勸諭所指出的,救恩歷史中天主的話語同祂的行動並無二致(註8),故此,今日我們舉行禮儀,祂的話語連同伴隨而來的轉化德能,正是吾人體驗神聖感的根本。 當我們將神聖感視為禮儀實踐的優先項目時,將發現聖禮的各個方面都能被歸到正確的位置及尺度上,處於和諧的秩序中。如果說羅馬禮的精神表現在理性、克制、適度有節、高貴的儉樸(註9),那麼直指禮儀本質的神聖感便是做好羅馬禮的一把鑰匙。在彰顯神聖的大前提下,禮儀人應當盡其所能讓聖禮的「事效」與「人效」充分接合,俾使天主子民在聖禮中蒙受天主恩寵的更新與轉化,持續行走於成聖的旅途上。天主藉著聖禮的儀節,賜給我們貴重的禮物,神聖的恩寵,而禮儀人要促成這禮物的寶匣被開啟,彰顯天主那更新並轉化我們生命的神聖。 註 [9] 此按Edmund Bishop(畢夏普)在The genius of the Roman Rite中提出的。
敬祝 您們在聖禮的參與及服事中,走上成聖之路! 禮儀研究中心 敬上 |
|||||||||
關於我們----恩人錄 (每月月初的感恩祭中,特別為禮儀中心奉獻的恩人們祈禱。) 衷心感謝所有恩人對我們的支持,我們方得為全球華語教會提供更多、更深入的禮儀培育及服務。 如果您想持續定期收到本電子報,或對於本刊及網站內容有任何建議、指教,歡迎與我們聯絡。若要取消訂閱,也請告知!(請點選下方小天使) |
|||||||||
| 版權所有 天主教輔仁聖博敏神學院 中華民國台灣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514巷103號  Copyright Fu Jen Faculty of Theology of St. Robert Bellarmine. No. 103, Lane 514, Zhongzheng Rd. Xinzhuang Dist., New Taipei City, 24255, Taiwan (R.O.C.) Phone: (886-2)2901-7270 ext.164 |
|||||||||